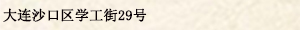深夜食堂我想吃甜酒冲蛋加小丸子加枸
吃这件事,说起来确实是神奇。老祖宗说,食色,性也,老祖宗还说,饮食男女。且不管他本身的意义几何,我想,食,性也;色,性也,该不会有人反对。吃,总少不了人做主,总少不了时间作祟:有些东西过去喜得吃,现在不愿吃;有些东西过去都不拿睁眼瞧上一瞧,现在吃得津津有味;有些东西和她吃得,和他却吃不得;有些东西一个人时绝不吃,两个人时却能吃出甜情蜜意来,一群人时也能吃出酣畅淋漓来。吃什么自然重要,入口的滋味是食物的身家性命,咸淡软硬,给它一个形容词就给了它一个于口齿间横冲直撞的身份,找到个能挂上一连串褒义词前缀的美味,吃点好的,太简单了。我要说吃神奇的地方,自然就不在于吃什么。而是什么时候吃,在哪儿吃,和谁吃。
女友喜欢喝酒酿,几乎次次在家叫外卖她都要点上一份酒酿小丸子,商家从来不吝啬,一次就送来满满一大碗,白白的,稠稠的,盖子掀开冷上一会儿,她的头就埋进了碗里,咕噜咕噜地享受起来。我不喝,就坐在旁边看她喝。今天晚饭的时候她拍了自己的晚饭发过来,我看到那一大碗,下意识地问她是不是又在喝酒酿小丸子了嘛。
她很快回:这个是南瓜粥。可是我倒是想吃甜酒冲蛋加小丸子加枸杞加桂圆加红枣了。我小时候外公每天都给我做夜宵,就是做这个。他说,马无夜草不肥。
我当下就明白了为什么女友到哪儿都不忘自己的酒酿小丸子了,她是被甜酒喂饱的,也是被甜酒喂大的,小时候吃的,总会是一辈子吃的。很不幸的是,女友说的那一长串吃的里,本来没有一个是我爱吃的。从小到大家里都没有煲汤的习惯,久而久之我对一切带汤水的东西都失去了兴趣,甜酒跟着遭殃。湖南人爱吃甜酒冲蛋,大年初一的早晨老家有在列祖列宗面前围成一圈喝甜酒的习俗,我最怕这个环节,每次都要在心里请求祖宗不要怪罪,才敢只抿一下碗边,就把碗放下。干货我也不大吃,小时候母亲总逼我吃枸杞、红枣、桂圆,说大了我就明白了,这东西对女人最好。可我受不了齿间的甜腻和粘稠,只要母亲把它们塞到我手里,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偷偷地往她看不见的地方塞,沙发下,茶几下,拿卫生纸包着直接丢进垃圾桶里。不吃的理由也并不充分,但我,就是,不吃。
拒绝汤水拒绝干货,我自然也就没有长成水灵灵的大姑娘或者顶天立地的硬汉。
但神奇的是,和女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吃的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她说,你也来吃一口嘛,我也就可以自然地蹭上去咕噜上一口。她说,我会做啊,以后做给你吃嘛。我乐不可支,全然忘记自己其实没有认真吃过甜酒冲蛋加小丸子加枸杞加桂圆加红枣,但听上去好像很不错呢。她总不会骗我嘛。
吃总是要分人的,和爱人吃的是情,和朋友吃的是义,和家人吃的是和气,和自己吃的难免是孤独。能让人自在又满足的吃法,无非就是和多少有过故事的人,就着故事,佐上经历,酣畅开吃。所以我很少武断地评价一个东西好不好吃:和她吃好吃极了,和他吃平淡无奇,自己一个人吃真是,灾难啊。吃的体验总被打上身边陪吃的人的烙印。比如女工的捞面(女工合作社,港中大校园里唯一一个营业到深夜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小食贩卖店),凌晨倾完pro走出大图和坡友径直走向女工,说一句,笑一句,一份捞面就能吃的油光焕发,我觉得女工有中大最好吃的东西;也在深夜被朋友拖出去过,穿着睡裤坐在看台上,聊心事,说一句,哭一句,一份捞面吃了两个小时还没能吃完,我觉得女工的捞面真的好咸;一个人闲着没事也会去吃捞面,权当果腹,但滋味全无。有时眼盲且心盲,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捞面还是那份捞面,我还是那个我,但感受却总不同。
除了人,吃也逃不开时间的手。我一向自称专一,朋友笑我早餐只吃楼下善衡的鱼柳炒蛋,一吃就吃两年,且饮料一定得是可乐加冰,夏天加冰,冬天加冰。但时间那双翻云覆雨手改变了的我的食性,我只是偷偷藏起来,不和任何人说。小时候从来不吃苦瓜,这名字听上去就应该入药而不应入菜,哪怕拿它炒了我最爱的鸡蛋,我也会气恼地连鸡蛋都不吃了,就是不肯臣服于它。直到近两年,突然就觉察出苦瓜的好来,清炒也好,炒蛋也好,生吃也好,清脆又青涩,怎样都好。后来听到陈奕迅唱:食得出它睿智越来越记挂。忽得也觉察出自己年长后的睿智。
其实早餐我也开始吃其他的了,即食面也吃,叉烧包也吃。饮料我也喝冻奶茶和七喜了,但加冰的习惯,还没能改。
吃这个神奇的动词、名词、形容词,从来都跟在人这个主语的后面,而人,不过是在和时间兜圈子呢。《苦瓜》里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歌词:那意味着他的美年轻不会洞察吗。也许,我们现在觉得好吃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年轻,能洞察它的美,而我们现在觉得不好吃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年轻,还无法洞察它的美。这样的祝福是有些中二,但还是要祝大家永远都能在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人,吃你后来想想都会觉得真好吃的东西。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永远的祝福一定会被辜负,但总无妨。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