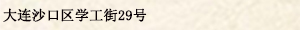隔离琐记vol02人成了需要ldq
因为我也经历了那个艰难的时代——且我很难说,在走出那个时代时,自己毫发无损、平静而纯粹,保持了内在的完整、成熟、勇敢、不妥协,没有被异己的思想观念左右。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另一种美》
1
1
1
生活的秩序感在瓦解。
像被雨水冲刷过的沙堡,一点点坍塌下去。
电视的新闻里响起胜利的号角,铿锵的语调,温馨和谐的画面。
电视外,人间是一座沙堡,苦难的坑洞,肃穆萧条。
舞台上刺目的灯光只够照亮一个人。伟大和信念在退场。
无端想把全部的精力投放到一件小事上去,
种花,剥蒜,清理毛衣上的毛球,地板上的灰尘扫了一遍又一遍。
看平时没有时间看的剧,一定要看拍摄花絮。笑出声。
花絮里的演员会念错台词,会笑场。两个演员在探讨吻戏。
导演出现在镜头里,指导,打趣。然后若无其事,继续拍下去。
他们知道,无论怎样,都会有下一次。
无论怎样,经过剪辑的画面里,一切都是完好的。
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场电影啊,念错台词的人再没有机会改正。
满世界找不到一个可喊“卡”的导演。
剪辑过的版本反而更让人愤怒。
生活本身如同一场绵延无际的梦境。
苦苦等着醒来的人,因为实在太过疲惫,最后真的睡着了。
1
2
1
去超市买下个星期的口粮。
尽量挑选那些已经贴好价签的,这样就不必排长队等称重。
那天我走到称重处,忘记是要称两个苹果还是三个水晶梨。
把它们放在称上的时候,三两个人朝我的方向走过来。
我慌忙拽起已经称好放在一侧的苹果,
却不小心碰掉了负责称重的售货员事先放在一旁的一根胡萝卜。
“你能不能慢点啊。”她凶极了。像在骂人。
在那极为短暂的一刻,我突然为自己的慌乱感到羞赧。
走过来的只是人而已,不是吗?
在旁边那位等着称葡萄的年轻男士看来,我一定是一个无礼又错乱的糙人吧。
对啊,可是,你究竟在怕什么呢?
1
3
1
那一次我真的发了脾气。这在平常极为少见。
距离社区最近的超市,大爷大妈和年轻的情侣人挤人挨在一起。
进门时测了体温,而我疑心那个体温枪不过是个摆设。
结账时排了好久的队。
前面有个快递员插了队,为买一包烟急不可耐。
自助结账,轮到我们。
一件件蔬菜和食品放到右手边的台子上,中途不能拿走装袋,否则机器会响。
物架堆满了,牡蛎的汤汁洒了出来,浸到了干净的牛奶盒。
结好账,正准备一件件装袋时,超市的售货员,一个鬓角发白的大爷,
吼道:“你们能不能快点?拿到车里推出去再弄不行?没见这么多人等着呢么?”
他的胳膊上戴着红色的袖标。
一种似乎只存在于历史,却时常在现实中重现的权力。小人物的权力,色厉内荏。
后面排队的人迅速投来一双双冷眼,仿佛是要吞掉我们一般。
我吼了回去。
不记得吼了什么,总之是吼了回去。
若是在平时,我从不这样吼别人,从不,吼任何人。
在超市里耽误时间,等于暴露在病毒的风险中,约等于离死亡更近一步。
那里,任何人都是任何人的敌人,抢夺时间的敌人,冷眼相待的敌人。
在一场不明结果的战役中。
1
4
1
远方的朋友为我订了一块蛋糕。
说是为了支撑开蛋糕店的朋友,好帮她在近期艰难的创业中存活下来。
我说,我给你朋友打个赏吧,毕竟我最爱蛋糕。
她说,就因为你在北京,蛋糕店也开在北京,两全其美。
于是我凭空多了一个星期的早餐。
下楼去取蛋糕,程序极为复杂。
口罩,手套,毛线帽,全副武装。
绕开楼下被封死的大门,走到西门。
向一群穿制服的人亮出自己的出入证,到居委会办的,必须人手一张。
绕过快递公司在门外支起的摊子,和聚在一起找快递的居民。
大门口的喇叭循环播放着:
“回家勤洗手,开窗多通风。不传谣,不信谣。
抗击疫情靠大家,安全幸福你我他。”
步行到路口,空旷无人的路口。
送蛋糕的小伙子麻利地从驾驶座下来,打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像迎娶新娘一样,双手捧出粉红色的蛋糕盒子。
我伸手刚要接。他另一只手从上衣兜里飞速掏出一瓶小小的喷雾。
他以近乎气急败坏的决绝方式,朝着我俩悬在半空的手狂喷。
然后郑重地将蛋糕递到我手里,隔着口罩说:祝您生活愉快。
酒精的喷雾散在空气中,瞬间不见,犹如无色无味的信任。
1
5
1
物业在居民楼的电梯里放了纸抽。电梯外的按钮边也有。
附上一张手写的卡片:
“请您抽一张纸按楼层键,纸不要扔,可用来垫着开门禁的按钮或楼层门后再扔。”
字体和语气都像个老人家,一种过度关心的道义感。
过不久,整包纸抽被拿走了。
又过了几天,单元门的门禁坏了。看那锁的样子,像是被什么人硬生生拽开了。
不,大概是被人用脚踹开了。
1
6
1
走到商场的大门口,我前面的人停了下来。
一个中年男人,油滋滋的短发在风中乱作一团。
他侧身装作看手机,似在用余光瞟向我。
我知道,他在等我替他拉开那扇门。
1
7
1
一家书店在求救。
这关头,求救的人怕是数不胜数。
有的声音听见了,有的听不见。有的现在听见了,有的将永远听不见。
常常觉得,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这个年代可留存的实在太有限了。
日日生活在无历史的城市之中,不谈政治是一种奢侈,谈政治却又会跌入另一种身份的危险。
推崇纪实的平台拒绝个人感受,只想要赤裸裸的“真人真事”,哪怕是为了创造戏剧性而编造生活的谎言。
小说期刊又拒绝写实,讲述太过平凡的人生等同于无创意和人云亦云。
读者们的神经被种种刺激物即刻填充——歌曲高音、搞笑综艺、造星节目、鲜艳却无深意的电影画面……
书籍对个人和社会都不再是必需品,人们宁愿花上千元买衣服、化妆品、游戏,却对几十块钱的书哭穷喊贵。
出版业渐渐走向夕阳末路,编辑们转向视频、直播、营销活动。
作者和翻译拿着低廉的稿费混沌度日。
写作者的行当变得愈发可疑。
书店正在死亡。
这个时代的所谓文化又何尝不是在挣扎求生呢?
不信你听,一家书店在求救。
1
8
1
不做无畏的争斗,但也绝不轻言宽恕。
不与低俗之恶苟合,但对作恶者从不惜狠话。
不介入蜚短流长,但万不肯残喘于夹缝。
不无故哀叹命运,但悲剧降临之时需保有悲伤的力气。
说出口的话不必非要被听见,但务必要真真正正说出口。
这大概就是一个人最后的骨气吧。
1
9
1
每隔几天,就会接到陌生人的电话。有时是一天接上几个。
居委会,租房中介,保险,英语辅导,心理咨询。
打电话的人听起来像人,多半是机器。
只需不停换着句式发问,就能轻易识别。语言学的小游戏。
唯独核查信息的人是真人。语调急迫。
几家药店里的发热药和咳嗽药通通被撤走了。
以防有人发了烧四处走动。若不严重就挺过去,医院。
去医院就意味着能被发现。
人成了需要“被发现”的物种,类似于冰川世纪的猛犸象。
要报告行踪。
要戴口罩,哪怕口罩并不能轻易买到。
要坚持体温正常。
不在公众场合咳嗽变成一种社交礼仪。
患了慢性咽炎的人是罪人。在家打麻将的人被掀翻了麻将桌。
在那座城市,存在一个凌晨三点钟的集市。
穿梭其中的人宁肯不睡觉,也要买上一兜菜。
一个女人,宁肯徒手爬下十层楼,也要去买一小袋猪肉。
在外人看,不过是天大的笑话。
而在那些人,却是生活本身。
1
10
1
一本书出版了。关闭了评分。
那长长的目录里,只有两种句态:祈使句和将来时。
这是独属于这个国度的语言特色。
人人都在等候传达,传达,以最直白的语句。
报告,口号,标语,文件。
用理想编织起一件美衣。
而衣服遮住的身体,无人关心。
1
11
1
作家们保持沉默。
说话的学者从网络上消失。
直播被掐断,哪怕是一节生理卫生课。
记者像一群手无寸铁的反抗者。
第一个说真话的人成了神。
人们调动毕生的经验和智慧,用于猜测。
“平安健康即是福”的信念隔代传播。
有时候,活着只是活着。
1
12
1
网友私信发来求助。
要么是病毒,要么是肺病的老父,要么是精神疾病。
他们大多来自三四线小城,倾其心血也抵不过一次危机。
而我是多么渺小,除了捐一点,再捐一点,还能做些什么呢?
劝慰是轻飘的,更像是隔岸观火。
一颗石子是脆弱的,精卫只能以身体往复,高低徘徊。
捐钱的人,已经够多了吧?
善良的人,已经够多了吧?
可是,为什么总填不满人间疾苦呢?
张畅(豆瓣
赫恩曼尼)90后写作者,节目策划人。
做过编辑、记者。
腾讯·谷雨、澎湃·湃客特约撰稿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
业余时间写作、采访、翻译
长按
| |